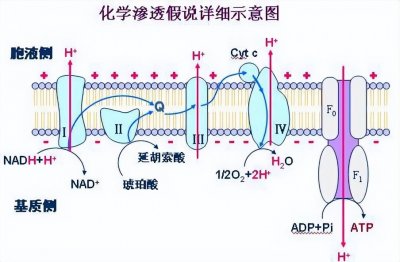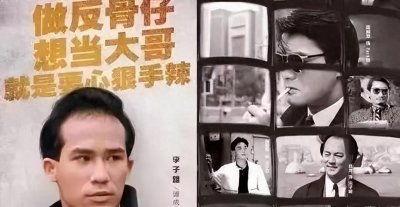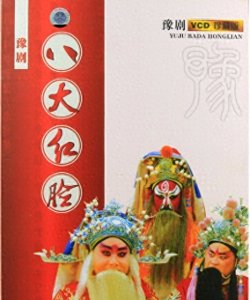红军主力长征后,我跟着谭余保打游击
红军主力长征后,我跟着谭余保打游击
夜过无名岭
1935年古历4月底,湘赣边区省委从江西武功山秘密转移到湖南攸县的狮子岭,暂作停留。这一走,我们着力经营了多年的江西苏区,便全部丧失了。因为经费困难,时任省委书记的陈洪时命令特务队立即出发,外出汝城打土豪,以解决燃眉之急,由白区工作组提供土豪对象和向导。部队于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,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便出发了。

油画作品:激烈战斗的红军
向导说:“现在天没有黑,山路走起来还方便,到天一黑,有些不好走了。要是下雨,就更麻烦。要过一个不好过的山,这个山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,当地百姓就叫它无名岭。”我对向导说:“当红军走夜路是家常便饭,每次出发都要走几天夜路,走山路也不怕,只要有路,就可以走过去。”向导说:“队长,那山就是没有路,尽是高的矮的树,一丛丛、一蓬蓬的草,白天走,要拨开草才能辨认出路来,晚上困难更大,前面走的同志要格外小心,走错不得了。走完几十里山路,还要过一个悬崖,很高很陡的山崖下是一条河,水寒刺骨,像阴河一样。人过悬崖,只能在岩石上慢慢挪动,稍有不慎,人掉下去不被摔死也被淹死,很少能活命。”
我一听,真有点心怵,夜路走过不少,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险境。天慢慢黑下来了,为了今天晚上行军安全,部队暂时休息,吃点生米,养点力气。我把向导讲的话向大家重复一遍,引起大家注意,以免发生事故。彭克生政委要求每个同志要前后照顾,不让一个人掉队。大约休息了半个钟头,部队又开始前进。天气越来越闷热,天上乌云翻滚,一层层灰黑的云块像要从天上掉下来。随着一声炸雷响过,雨点哗啦啦地在在头上乱打。同志们凭着一双爬惯了山路的脚,在闪电的蓝光下,从黑黝黝的山林中,眼睛看着脚下,耳里听着喳喳的雨声,脸上擦着一把又一把的雨水,一个跟着一个,艰难地前进着,速度慢得烦心。有的战士跌倒了,爬起来又走,你起来慢了,或前或后的人就会搀扶一把。
一百多条英雄好汉,为了革命的需要,从不计较什么。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想的,不是豪言壮语,不是激昂表态,而是非常朴实地盼着早点赶到目的地。在山里摸着走着,时间一点也不吝啬,两三个小时究竟走了多远,向导说,大概走了十来里。天啦,平时走夜路,这么久时间,早已走出三四十里地了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:“这革命的路真不容易走。”我们走着走着,夜风小了,雨也停了,云在飘散,渐渐露出星光来,大家的情绪高涨,速度也快了一些。
又走了三个多小时,树木稀少了,前面黑压压的一座石山,向导说:“悬崖到了。”我命令向后传:“悬崖到了,小心脚下。”下过雨的石崖很湿,战士们更加谨慎,一个个前脚跟后脚,人扶人,担心滑倒,更担心掉下悬崖,好半天才能前进一段路。忽听“哎哟”一声,一个战士掉下去了,接着又听到叫喊“救我”,惊心的呼声使每个人的神经更加紧张。原来,这个战士被悬崖下的一棵树挂住了,没有掉到底,同志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他拉上来。战士们只差用手抵在崖石上爬了,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,比一次长途奔袭还辛苦。
天快亮了,悬崖也走过了,问问向导,到目的地还有多远,向导说,走了一半的样子,彭政委说,这趟行军太辛苦了,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宿营吧,大家就靠在石山下避雨一点的地方躺下了。阵阵南风吹过,天上显出鱼肚白来,一会儿天开云散,一轮红日喷薄欲出,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。
脱 险
我们于五月初二来到柏树下,这里原是游击区,山深林密,群众基础较好,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两天。我和彭政委研究,应该兵分两路,他和大多数人在这里待命,我带15人出发。通过茶陵,来到酃县的一个竹山林里休息,随即派出两个小组外出侦察。第一组有曾秋同、贺丁九、刘泉三人;第二组有甘同生、谭录、谭发达三人,一前一后,互相照应。
第一侦察组走出有三四里路,在一个竹林里碰上一个青年人在砍竹子,曾秋同上前问话:“砍竹子作什么?”青年人答:“砍竹子运出去卖。”曾秋同想了解附近有没有国民党军队,青年人不正面回答,反问曾秋同你们是什么人。曾秋同觉得这个青年脑子活,心里有话,便说:“你看我们是什么人?”青年人说:“我看你们像红军。”秋同说是红军,那个青年人说:“喂,有个姓傅的你们知道吗?”虽然是一句很普通的问话,却是一句接头的暗号,曾秋同正要回答,甘同生来了,见了这个青年就招呼:“小陈,你在这干什么?”原来甘同生和我到他家吃过饭,所以认识他。小陈忙说:“傅叔叔来了吗?有重大情报要告诉他。”两个侦察组的人和小陈回到驻地,我问小陈:“你父亲要你来干什么?”小陈说:“我爸要你立即到我家去,有大事要说。”
我带了刘全、曾秋同两个赶到陈家,陈大哥见我来了,急忙把我拉到屋里,告诉我省委书记陈洪时十几天前已经叛变投敌(陈洪时于1935年6月12日叛逃),带了一大帮人。他们正串通驻军和保安团围剿你们,他们骗你们来打土豪,是送肉上砧板,你们赶快回去吧,不然会全部被消灭的。我听了这个消息,有如惊雷轰顶,便问陈大哥:“你这消息可靠吗?”“怎么不可靠,县委要求各个联络点派人守候,打听到特务队来了,立即告诉你们。”
我想了好久,心中半信半疑。在他家吃过中饭,马上找当地百姓打听,百姓中也传说纷纷,有一位张大叔说:“陈洪时带一帮人投降国民党,说还有一支队伍自己送上门来,那不就是你们吗?”我问:“这里原来有白军吗?”张大叔说:“原来没有,就这一两天来的。”我一想,形势相当严峻,我要刘全拿几块银洋给张大叔,请他为我们带路脱险,张大叔说:“带路可以,钱坚决不要。我是老农会会员,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。只要你们相信我,我一定把你们带出去,他们不能条条田埂都放哨的。”这句话使我们更添信心和希望。
我命令曾秋同立即集合队伍,跑步来这里集合,跟随张大叔突出包围。张大叔问我朝哪个方向走,我说朝北的方向,于是我和曾秋同随张大叔在前,刘全、甘同生在后,便从竹山林里小路穿山越岭,不走人家屋门口过身,怕狗叫惊动人家。一路上边躲藏,边走路,不知绕过多少村庄,走过多少田坎边,到黄昏时候,大约走了二十多里,快到警戒线了。天黑下来,没有月亮,十来米远就看不清人,只能凭听觉辨别情况。我们正要下一个山坡,忽听得一声喊:“什么人?口令!”我们紧张万分,立即原地蹲下,准备战斗。随即又听到一声答:“围剿!回口令!”“胜利!”问话的一方回了口令,原来是双方巡逻警戒的碰头了,然后各自回转。多险!我们立即在山头屏住气,一直等他们远了,才敢下山。

谭余保
又走了二十来里,到了河边。张大叔说:“过了河就好了。”一看码头上,没有渡船,我要曾秋同带二人去找船,不一会,秋同从水下推着一条船靠了岸。我们和张大叔要分手了,刘全拿出六块银洋给张大叔,张大叔坚决不要,我们非常感谢张大叔为我们带路。大家依次上船。走进船舱一看,还睡着两个保安团的兵,我们把这两个人抓来一问,知道是保安团派他们来守码头,防止“共匪”过河。他们把船停在河中,自以为很安全,谁知做了我们的俘虏。
过了河,又在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下,总算脱离了险境,安全回到柏树下。
十里茅山
我和彭克生政委研究如何回到省委身边。狮子岭肯定不能去了,现在只有两个地点:一是莲花县委吴金莲处,一是攸县县委甘有贤处。可是,最近都没有联系,谁知道这两处被破坏了没有。正在为难之际,省委交通员彭连生同志来了。他详细说了陈洪时等人叛变的事,都是背着谭余保干的,现在省委只剩下谭主席一个人了。如今住在莲花垅上丝瓜塘。听说攸县县委物色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叫茅山,他要求我们去实地察看,以便省委转移。我们于古历八月下旬的一天,在攸县县委派来的向导引领下,向茅山行进。秋高气爽,金风飒飒,满山红的黄的树叶,风景实在好极了。四周出奇的宁静,偶尔有几声山鸟的鸣叫,听起来非常悦耳。深山的夜风,吹得人一阵阵发凉。我们满怀信心地前进着,在凌晨五点终于走到了茅山。
茅山,确实不假,眼前不见树林的影子,尽是深没人头的茅草,密密麻麻,无边无际。山沟里的茅草由于地势低潮,长得约有一丈多高,古人说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,在茅山,风吹草低连人也见不着。在这样的地方隐蔽下来,只要内部不出叛徒,敌人是无论如何也找不着的。我们在草地的边缘休息,吃点生米,到早上八、九点钟的时候,扒开茅草,继续向腹地进发。甘同生、刘泉二人走在最后,扶起被踩倒的茅草,清除痕迹,防止敌人跟踪。大约走了两三里路,从茅草尖上隐约看到前面有座山。向导说,那个叫甘子山,山脚下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大家听着,更来劲了。
大山脚下有一条河,绕山咀而流,河面宽有十来丈,河面像镜子一样平静,河水青得发蓝。水温清凉清凉的,我们不敢生喝,水寒伤骨呀。河南岸是连绵的山,山顶上树木葱茏,山崖上的茅草,像草帘一样垂覆下来,把山崖全盖住了。如果在山脚搭个窝棚,这些茅草一盖,外面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么理想的地方,真是天下无双了吧。
晚上,我们就在河北岸的茅草里宿营,在营房的边缘放了四个游动哨,以防野兽的袭击。第二天下午两点,太阳晒得河水稍微好点的时候,游过河去,在南岸的山崖下搭了几个窝棚。于是,要向导回去向攸县县委汇报,把谭主席从莲花接过来。九月初,谭余保主席从莲花秘密来到茅山,看了这里的地形和我们搭的窝棚十分高兴。他说,只要不出叛徒,住个三年五载不成问题。
调虎离山
保卫省委谭主席来到甘子山,由于有叛徒告密,敌人很快调动莲花、攸县两县的保安团和部分国民党军队,连叛徒周捷在内,包围甘子山,并向茅山进击。于是谭余保同志在特务队护卫下转移。为了防止意外,我要谭录、谭惠也到前面去保护谭主席,小云给了我两个手榴弹,我一看,还是苏联红军送给我们的武器,分量重、威力大。
我们正在行进中,“哒”一声响,前面一个尖兵应声倒下,我随即甩了一个手榴弹,把敌人的枪手炸死了,趁着烟雾弥漫之际,我拾起尖兵的枪向敌人射击。这时,特务队的火力已经打得敌人抬不起头,我要贺丁九领着谭主席等大队人马向西南边山脚隐蔽转移。根据当时周围的态势,除南边外,我们已三面被敌包围。若要是在小树林里,我们所有的人一定被消灭,好在这里是茅山,地方大,茅草深,敌人一般不敢贸然进入腹地,刚才是遭遇,敌人没有后续部队增援,打过了就完了。
现在唯一的办法,是派几个人用调虎离山之计,把敌人引向十里茅山的北面,引向与谭主席转移相反的方向,用少量的牺牲来换取谭主席和大部队的安全。敌人不是说捉住谭余保,湖南、江西、广东三省就平安无事了吗?敌人不是宣扬活捉谭余保,赏银十万元,死尸也赏五千吗?所以,保卫谭主席就是保卫革命,就是保卫共产党。
这时,叛徒周捷露面了,他叫喊:“谭余保,只要你过来,我担保你生命安全!”“共产党没有希望了,你何苦受罪呢?”周捷还点了我的名,要我投过去当保安团长。
谭录、谭惠两个小青年想打死周捷,我反复向他们解释保卫谭主席的重要性。叛徒的脑袋暂时留着,以后会有机会处决他的,你去打他,不一定打得着,反而暴露了目标,敌人一窝蜂就围上来了,你自己也回不来,所以,革命不能逞一时之勇,还要有智谋,能分别轻重。经我一说,他们二人总算明白了,不一会,贺丁九返回来了,他说,谭主席要他去打叛徒周捷,我拦住了他,把刚才和小谭讲的道理再讲一遍,叛徒如此嚣张,正是找不着目标,巴不得你去打他。
小贺说,不打不行,我不去,谭主席会要我的脑袋,我说,你再去向谭主席说,就说是我说的,在这危急关头,千万不能暴露目标,只能用调虎离山之计,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,然后谭主席才能转移。你向谭主席说,我傅云飞愿意去引诱敌人,他们说,我们也愿意,陈长也说:“我跟你去。”我说:“你们愿意去。很好,有四个够了。”我要陈长与贺丁九去向谭主席汇报,交代贺丁九集合地点和接头暗号。不一会,陈长回来了,说谭主席同意你的计划,还表扬了你。
趁敌人吃午饭时,我们四个人分两处同时开枪,向北突围,搅得茅草乱动,敌人急忙放下饭碗,大喊“冲呀,谭余保要跑呀。”这一喊,敌人像水鸭子一样全都朝北赶来,调虎离山之计初步实现了。我们四个人分开搅动茅草,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动似的,敌人朝茅草动的地方打枪,我们有茅草掩护,又在暗处,根本打不着,而我们却可以朝他们射击,叛徒周捷看到我们打死了他们的人,突围往十里茅山北面去了,急得大叫:“谭余保你跑不了,弟兄们快追呀!”莲花、攸县的保安团头子眼看到手的赏金得不着,便训斥周捷:“拿不到谭余保,唯你是问。”这一来,周捷叛徒的气焰才没有那么猖狂。
九月的天气,刮着南风,茅草干燥,到了下午两点,叛徒周捷又施毒招,放火烧山。山火一起,无边无际的茅草渐渐成为一片火海。眼看大火将要把我们包围住,谭惠沉不住气了,说与其被火烧死,不如出去拼,我说不行,我们的计划已经实现,我们如果去拼,四个人一下就拼完了,敌人一看再也没有动静了,就会识破我们的计划,调转头再去围捕谭主席和大部队,岂不是因小失大吗?如果真的烧死了,为革命牺牲,也是值得的。
我们四个人躲在草丛中,企盼着敌人全力追来。大火呼呼地燃烧着,发出啪啪的爆炸的声音。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,忽然黑云翻滚,电闪雷鸣,顷刻之间,瓢泼般的大雨像倒了天河似地倾泻下来,很快把大火浇灭了。叛徒周捷长叹一声,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不可强也。”敌保安团头子气得要杀周捷,讹他个“谎报军情”的罪名,周捷急忙跪地求饶,苦苦哀告,才算保得他的狗命,夹着尾巴跟着主子们走了。
酒肉擒敌
我和谭惠赶到集合地点,陈长及谭录已经在那里了。谭录见了我们,非常高兴地告诉我,谭主席时刻在挂念你。不一会,谭主席出来了,一见面,他握着我的手说:“好同志,你们辛苦了。那一把火,我真担心,现在回来就好了。”接着,研究如何去莲花找莲花县委。我说:“最好的办法是化装成保安队,这样比较不被注意,否则,敌人总会察觉的。”我们正在商讨时,有交通员前来报告,我们有一个姓王的联络点来了三个陌生人,要在点上过夜。我估计是敌人的埋伏,要陈长带三个人去看看。
到了联络点,陈长走过去机警地对他们说:“你们这几个共产党的探子,是想接谭余保的吧,给我抓起来。”有一个披着青褂子衣的人说:“不是不是,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探子,我们是莲花保安团的,因为没有抓住谭余保,不知他往那条路上走,要我们埋伏在这里。”陈长问:“你们有多少人?”“这里三个人,上面有个纸棚六个人,再上去里把路有个大点的纸棚,有一排人。”“还有吗?”“没有了,他们都回去了。”“那好,你们在这里呆着吧。”“你们是······,”“我们是攸县保安团的。”“啊,原来是一路的。”
陈长回来后,把他的计划说了,利用王大哥给他们送饭的机会,明天中午做好菜,多送点酒,把他们灌醉,剥下他们的衣服,化装成莲花保安团的人,大大方方到莲花去,敌人肯定始料不及,比秘密转移更易于迷惑敌人。谭主席觉得这个办法好。
第二天上午11点,我们都作好了转移的准备工作,先把联络点的三个人和小纸棚的六个人抓起来了。12点,王大哥给大纸棚的敌人送去满桌的肉、鸡等好菜和三十斤米酒,这些家伙有酒有菜,吃得满嘴油光,排长有点醉意,乘着酒兴说:“老乡,再来一大壶酒。”王大哥又送去十斤米酒,结果吃得大醉如泥,都被我们抓了。一共抓了41个保安队员,我们把他们处决后,利用他们的服装、枪支等,我化装成排长,陈长、曾秋同是班长,其他的人都是战士,谭主席夹在人群中间,刘全、谭录在后,儿十双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路过时所遇到的一切,毫无阻拦地到了莲花县境。当晚,我们派联络员找到莲花县委,又重新开始战斗了。
开辟九陇山根据地
1936年古历9月中旬,久雨初晴之后,阳光特别温暖。特务队的同志们多在屋外晒太阳。谭余保也来了,吸着他能装一两干树叶的大竹根烟斗,一边吐着烟雾,一边发着感慨。那个时候,形势真是非常严峻。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,在敌人严厉的围攻下,湘赣边区所属湖南、江西两省的根据地,儿乎丧失殆尽。省委蛰居莲花丝瓜塘一隅之地,需要另外开辟据点。谭余保说:“听说井冈山北面有个九陇山,那里山大林深,地形复杂,群众基础也好,敌人占据井冈山后,也不敢轻易深入九陇山区。现在不知情况如何?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九陇山那里的人。”其实,陈长、彭连生和我,都是九陇山附近的人。当年我在地主家做长工时,时常在九陇山出进,那里的沟沟壑壑,我基本都熟悉。于是,谭余保就要我挑选几个人去开辟九陇山。
我挑选了陈长、彭连生、曾秋同和刘全四个人,领了三个月的伙食费,还带了1000块银洋作为救济资金,于九月十六日吃过早饭便出发了。走了三天,越过界化陇马路,于十九日黄昏时候来到花竹,进入九陇山。

红军烈士墓
九陇山,山西属湖南茶陵,山南属江西宁冈,东北属莲花,山形像个大斗笠,周边二三百里。山下有乡村集镇,越往里走,人口越少,一个山坳里有一户两户人家,大一点的也不过四五户,他们多住在半山腰,靠卖竹木材和竹木器具为生。花竹这个地方,我过去来过,山腰上住着一户彭姓贫民,老大彭光生和我很要好。我们走近他的屋,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我喊开门,说明来意,很受欢迎。老大摇着我的手臂说:“只要谭主席还活着,我们老百姓就有盼头了。”晚饭后,他们反映了当地敌我双方的许多情况,并建议我们要镇压安坑那个坏透了的保长,他经常带人讹诈老百姓的钱财,稍不如意,就说你通红军,今年有三四个人死在他手里。只要镇压了他,群众就起来了。
三天后,我们来到大水口彭天生家,他原是共青团员,是个篾匠,做竹器外卖。他反映小田圩和七里船两处有散兵活动。我告诉他,小田圩那股散兵,可能是今年五月在皮坳被打散的红五团的战士。我要他做我的联络员,把那股散兵引过来。随后我们又来到狗窝里。这个地方可说是九陇山的心脏地带了,山深林密,大山包套着小山包,犬牙交错,陌生人走进去,搞不清哪是来路,哪是出路。过去有人在这一带打过游击,群众觉悟相当高。这里住有四五户人家,有个谭明,过去和我很好。
他家用手工生产黄草纸,这几年兵荒马乱的,没有做草纸了,几个纸棚闲着,虽然破烂,只要稍加修葺,就可以住人办公,我们正好利用它。我们在这一带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把住在狗窝里周围十冲八坳的人家都走访了,当他们听说我们是谭主席派来的工作组,是来发动群众,组织群众干革命的,无不欢欣鼓舞,积极拥护,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,真正成为鱼水关系了。
十一月初三清晨,大水口的彭天生来找我,红五团被打散的战士们推荐一个排长来接头,我要他把排长带过来。第二天,彭天生和那个排长来了。经过详细询问,确认了他们是原红五团的战士无疑。又过了两天,那个排长把全部60多个战士带进狗窝里。他们不成建制,衣服破了,人也瘦的不像样,20多条步枪,只有几十发子弹,真难为他们,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,还是坚决不投降。自从他们来后,我拿出一些钱委托彭天生、谭明两人买了大米和布匹,解决了他们的衣食问题,又新盖了几个茅棚,作为安身之地,同志们非常高兴。
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,我们镇压了安坑那个欺压百姓的保长,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,无不拍手称快,赞扬工作组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我们组织群众打土豪、分粮食,又筹集了一大批款子,这一来,声势就造大了,老百姓的心向着共产党,向着红军。我们五个和那位排长共同商议,成立一个游击中队,下分五个小队,我和排长带一个小队住狗窝里,陈、彭、曾、刘各领一个小队分住花竹、大水口、龙狗洲和到坪,配合积极分子开展工作。预计在年底前回省委汇报工作时,再增添一批人马,向四周扩展,使九陇山中心地区成为我们立足的据点。
收服陈培珊
在九陇山站住脚后,我们侦察到七里船有一股土匪,约六十余人,那个头子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,叫陈培珊。这个人比较正直,纠集一些农民出身、本质不坏的散兵游勇,在七里船安营扎寨。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,不抢老百姓的东西,专找地主大户和买卖商家,实在搞不到,就饿肚子。当土匪还饿肚子,这是亘古没有听说的事,可见这个人是可以义取的。
1937年春节来了,我们几个人商量,送点过年物资去,加以说服,把他们收过来不是没有希望的。大家都说这个机会好,于是从我们打土豪收集的物资中,拿出100斤大米、100斤猪肉,40斤腊肉,还有小干鱼仔、黄花菜、海带等,又拿了一腿我们腌制的老虎肉,于腊月二十九,由我带四个人,打扮成当地老百姓,挑着担子,送上门去。陈长不放心让我去,我说:“别人去,我还不放心。我自己去,可以随机应变,我是本地人,他们不会怀疑的。”
我们五个人走进他们的驻地,有个哨兵拦住,问我们干什么的,我说过年了,我们老百姓送点东西给你们过年。哨兵见我们挑的大米、猪肉,高兴的不得了,连忙喊:“营长,有人送东西来了。”陈培珊听到这消息,马上跑出来,一看,真的是老百姓送的过年物资,便把我们请进屋,说了好多感谢的话。我见他如此诚恳,便试着问:“你们过年了,准备了好多吃的?”“没有准备什么。”“那不到老百姓家里抢点来?”一脸菜色的陈营长说:“国民党平时抢老百姓的东西,过年了,我们又抢老百姓的东西,那太对不起老百姓了。”我看他还有点良心,便说:“陈营长,我们要走了。”他很礼貌地说:“对不起,今天没有好招待,你们是哪个村的?过了年,我到你们那里拜年。”说罢,叫副官拿出两支枪给我们,叮嘱下次国民党再来抢,你们就打他。
我想正好劝说,便推辞道:“营长,我们不要你的枪,我们想要你和红军合作打国民党。”他听我说红军,望了我一会儿,知道来者不是一般百姓,便叫他的士兵走开,然后单膝一跪,两手一揖说:“敢问你们是红军吗?”我连忙也一跪一揖,和拜把兄弟一样,把他扶起来说:“我们正是红军。”他高兴地说:“红军兄弟,我老早想去投降红军,就是没有人引荐。今天你们来了,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你们在哪里住,明天我就带队伍去投诚,你们收不收?”我说:“陈营长,你愿意参加红军,我们欢迎,但也不急在一天两天。过了年,请你和你的弟兄们讲明白,愿意当红军的就去,不愿意去的不勉强。”陈营长点头同意。我们约定正月初五再上门来。我们回到驻地,大家又讨论了一番,认为收服这支队伍的希望很大,便在山上加盖了好几个茅棚。陈营长有家属,我们给他另盖了一个。
到了约定日期,我和陈长商量好,部队在外面警戒,我一个人单刀赴会,如果陈某人没有诚意,我相信他也不至于杀我,等我出来,就消灭他们。如果有诚意,我和他在前面开路,你们就径直回来,不要露面。我走近前,陈营长带了十几个人在门外接我,进屋后,他们立正向我敬了一个军礼,陈营长说,我们全体官兵都愿意跟随红军打国民党,并把两本花名册送到我手上,一本是人的名字,一本是枪支弹药数,我大略看了一下,枪支和子弹都少得可怜。我说:“陈营长,欢迎你们参加革命。”
我们谈论了好久,陈营长又领我到他家,他的父母妻子都很客气,他父母对他说:“你要在红军大哥面前对天发誓,今后绝不三心二意。”陈营长真的跪在大门口说:“我陈培珊对天发誓,至死跟红军不变心。”我急忙扶起他,勉励他只要有决心,革命迟早会成功的。我问什么时候动身,他一个立正,“马上集合出发。”于是我和陈营长在前,全体官兵在后,开到了我们的驻地。陈长等人也已回来,站在棚子前面欢迎。这一来,我们的人多了,新老队员混合编成一个大队,三个中队,并划定活动区域,相互之间约二、三十里,一个五六十里范围内的革命据点形成,一支红色游击队也初具规模了。
傅云飞生平简介,傅云飞,原名傅云仔,茶陵县秩堂乡人,1928年参加红军,解放后曾在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湖南郴州地区任职。1958年调任湘钢纪委书记,在早期革命生涯中,傅云飞出生入死,对敌斗争英勇,灵活机智,参加过无数次战斗,经受了革命战争的长期考验。
(傅云飞口述 公常整理)
标签: